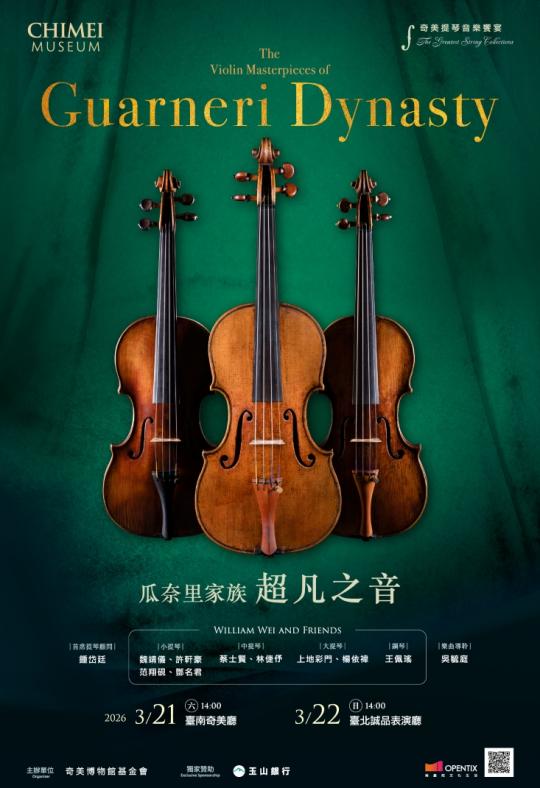為柔軟的石頭雕上剛強的心-石雕藝術家樊炯烈

遠遠地就看見了那個高大的男人開車駛向黃褐色的小屋,方才在路上的交會;小型的轎車中,看不出他的身形,直到他走下了車,高大的身形與隨性披上肩頭的長髮,真的是十足藝術家的模樣,反差的是搭在他臉上開懷的笑容。緊接著出門迎接的,是他的牽手與四隻如同老家人的狗兒,狗兒稱職地汪汪叫著,而他們夫妻倆,站在院子旁指引著我們停車方向,屋前的一漥池水以及屋後的一片田野,一座老屋與一棵大樹,在四落的石材與親切的笑聲中;我們已經來到了藝術家樊炯烈的工作室,低調而樸實無華的氛圍,甚至連GOOGLE地圖上都還沒有標註定位。


樊炯烈的工作室在台南大內區,大內已有十多位的藝術家在此地興起工作空間,尤其對雕塑石材的樊炯烈來說,市郊相對實惠的地價與更寬闊的空間尤其合適。1972年出生在台北的他,最後選擇落腳台南,不僅僅是因為需要藝術創作的空間,也是因為他對田園生活的一份熱愛。他說:「學生時期就到處在雕塑工作室打工,老師們的工作室大都在鄉下,他們習慣找個地方靜下來,而久了不只是習慣了,也愛上了鄉下生活的恬靜自在。記得當初朋友介紹來看這塊地時,我看見門口的大葉欖仁,樹型就跟我的『樊』字一模一樣!於是我更相信這是緣分,也就這樣住了下來。」語氣間充滿的藝術家浪漫;也就此定錨,小屋周遭更是延展了他對生活的想像,像是最近迷上的鹿角蕨也掛滿了小屋的窗櫺。


能有這樣愜意的風景,樊炯烈是珍惜與感謝的。談及五年前,他毅然決然辭去了旁人看似穩定的教職工作;返回鄉野專心創作,當時面對未來,他沒有徬徨;因為他知道自己若要下這個決心,就得面對旁人所謂的收入不穩定。在那五年中,他努力地持續創作,也因此接下許多建築案場與公共藝術的大小案子。
回想起教學生涯的喜悅與苦澀,樊炯烈簡單地說:「我想著當初為什麼會進入教學工作,是因為我喜歡雕塑,想藉著這份工作分享給更多人。喜歡雕塑是我的初心,但到了最後,我發現我已經沒時間和心情去創作,領著一份不快樂的薪水,被工作趕著生活,於是就決定專心回到創作這條路了!」


一時半刻許多情緒湧上,樊炯烈沒有繼續說話,接上的是另一個溫柔的聲音:「看他做事情,真的是全心全意,好像有一種使命感,尤其看他在做作品時,那種專心和耐心根本是一個吹毛求疵的境界!但就算如此,我知道他是真的很快樂的!」繼續說話的人,是樊炯烈的妻子黃雅智。
她總笑稱自己是不懂藝術的素人,與城市出生的樊炯烈孑然不同,黃雅智來自南投國姓鄉的山野間,人們暱稱她是枇杷公主,笑起來也十分大方親切的她,卻反差地有著一份具有穿透力而不造作的細膩,看著她順手遞上的水果,看著她小心拾起樊炯烈隨意擺在椅子上的茶杯,看著他們同一時間的大笑,看著他們不用多說一句的默契,頓時一種感同身受的溫暖和開心也在談笑間油然而生,樊炯烈說他真的很感謝雅智,在他陷在創作的選擇和迴圈中時,雅智的意見總是明亮而可信的。

在黃褐色的小屋,門外有著美麗的磨石子地,屋內也特意留下了老房子的結構,形成挑高的視覺。小而美的空間裡擺放著生活的氣味與樊炯烈的作品,他說:「我喜歡把作品的量體先放置在空間中,慢慢看著這塊石材或木材在空間裡的樣子,去思索那個感受,再慢慢去琢磨去想像。」他起身站到倚著窗光的一個作品旁;一座約90公分高的觀音石量體,將自然型態的石塊,大刀闊斧地切成了整齊的直角向上堆砌,最上方的尖角則留下了如山峰的形狀,樊炯烈說:「那時候我想像的是台灣的山區,總是時不時來場西北雨,當大雨落下就會在山峰間流下如溪水般的模樣,對我來說那個景色是我想留下來的。這個作品叫《山風雨落》,除了對山的刻畫,也是因為那句話『阿爸親像山』,是我紀念我父親的作品。」雖然後來得知,樊炯烈的父親始終沒有看過這個作品。在剛辭去教職的日子裡,樊炯烈開始埋頭創作了一系列的石雕創作,但也在那段日子中,父親的軀殼離開了這個世界,他說著那一天接到二哥打來的報喪電話後,他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,只記得那天的眼淚也像台灣山區的午後西北雨。

對很多人來說,大型雕塑好像一種魔法,好像「咻」地一瞬間就出現在公園的角落或是廣場的中央,也許也是因為它們的造型和量體總是看似大而完美,總有種「理所當然」擺置的感受,對於這樣的理所當然,就如同那些被忽略的創作過程。其實有時候更能藉著大型的創作,來打開每個人眼中細微的觀察力,能從遠觀的形體感受,也能近距離觀察蘊藏其中的故事。

樊炯烈的名字似乎天生就很適合石雕創作,有著剛強而烈的印象,但看他所做的作品就好像反映著他自己,在高大壯闊的身形裡,卻有著圓潤飽滿的心,經歲月的雕琢磨練,不僅僅是呈現了石材的紋理和塑形,同時挾著如山水畫作般的輕盈、簡單自在的童趣以及大孩子般的真性情。也許雕塑的創作過程對一般人來說甚難理解,但樊炯烈的石雕並不遙遠,也不生冷,反而像一座植栽也像一幅窗景,可以感受也可以閱讀,就像這天來到大內的田園風景;就像他們倆人的笑聲,皆是那般細緻而自然。